
我是不太喜歡柏樹的。
不好看,年紀輕輕的看著就很滄桑,沒有一點朝氣,皺皺巴巴、土里土氣,樹冠也小,哪有雪松氣派。
也不像構樹利于攀爬,可以躺在樹枝上聽風觀影遐想,夏天還可以摘幾顆紅果吃。
唯一的好處是,柏樹枝燒火真不錯。因為富含油脂,火力又急又旺,而且噼噼啪啪的,好聽!

綠意盎然的側柏
不知是不是其貌不揚的原因,現在鄭州城里很少見到柏樹了。現在的孩子,也不再把燒火當作游戲。
構樹也很少見了,誰還記得紅果的味道呢?
如今的馬路邊,都是漂亮的法桐、銀杏、白蠟、欒樹,柏樹和很多仿佛很遙遠其實并不遙遠的事情一樣,漸漸淡忘。
直到今年夏天,當我走進登封中岳廟——人生中第一次,被柏樹震撼到了。

路旁的側柏
準確地說,是側柏。
不是一棵兩棵,三棵五棵,而是三百多棵!它們遍布于廣闊的寺廟,路旁、墻邊、殿前、庭院,或高聳入云,或亭亭如蓋,或虬曲怒目,或沉默如山,仿佛廟中真正的神,活著的仙!
不是十年百年,而是五百年八百年、兩千年三千年!
三千年,幾乎就是中國歷史了。
文明初啟,諸子百家,英雄四起,盛世燦爛,百年血淚,革故鼎新,紅日東升,改革開放,龍騰復興……
所謂滄海桑田,除卻巫山,不過一棵樹的時間。而且,似乎來日方長。
如果我們可以活三千年,你敢想象嗎?我們現在應該做點什么呢?還會為今日憂明日愁嗎?還會耿耿于懷嗎?還會念念不忘嗎?如果有那么多煩惱,我們該有多么強大的意志才能度過這漫漫千年?

枝干直沖云霄
千年的側柏,變得好看了。
仿佛千萬條木之靈匯聚在一起,去偽存真,凝結蓄勢,漸成磅礴偉力,扭曲向上,直沖云霄,在空中炸裂,極盡舒展,恣意狂卷,無從定勢。
什么評價,什么標準,統統退下,這是側柏自己的定義,稱之為美。
色之美,勢之美,力之美,我之美,獨一無二,你學不會。
那種力量,所有的藝術形式都無從比擬、力不從心。
哪怕不遠處守庫的千年鐵人,也黯然失色;哪怕殿前張牙舞爪的石獅,也止于驚愕;只有屋脊上的騎雞仙人,笑而不語,如露如電,當如是觀。
站在這如神物般的側柏前,我頓悟了真正的力量,源自我心。
在這山神般的側柏林間徜徉,感覺紛繁歷史正在具象,無數的身影穿梭其間。
他們,莫不是你我,莫不有一顆赤誠之心,莫不是苦苦求索,安得廣廈,理想之國。

側柏的樹干
我不必知道,三千年間的人們,為什么一再種下柏樹。
他們也不必知道,三千前后的夏天,一個嬰兒靜悄悄地熟睡在樹下。
故事不會停止,悲欣循環往復。
這里是天地之中,周公立圭授時文明初啟的地方,居中守正,允執其中。
庶民的悲喜,也無非風調雨順,安居樂業。
我看著參天的古樹和樹下的嬰兒,恍然如夢,宛如新生。
而在東去六十里的超化寺內,那棵隋朝所植的檜柏前,在我舉起相機的剎那,一只喜鵲疾馳入鏡,仿若趕來叩首參拜。
這一刻,喜鵲,嬰兒,我和柏樹,是一個還是四個?
這無盡的時間無數的我們,是陌生的還是親近的?

飛檐與柏樹
晚上看捷克電影《花園》,洪荒、明媚、靜謐的東歐鄉村,陷入困頓的男主,先知般的牧羊人,盧梭和維特根斯坦,神秘少女,所有的問題都會被螞蟻愈合,擔心被野兔吃掉就變成一棵蘋果樹。
馬丁·舒立克的花園,破敗又神秘,具體又抽象,讓我想起老家的院子。
雖然只有一棵棗樹、一口破缸,幾雙曬得褪色的球鞋,雖然已經荒蕪蒙塵,卻永遠令我夢中神往。
它的意義,就是沒有意義。它不具備任何功能,就像人生不必全是目的。因其無用,所以它是奢侈的,浪漫的,游離的,充滿著各種不切實際的幻想。
它不屬于現實,它是詩歌。
就像一棵樹。
編者按
“要把古樹名木保護好,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好。”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,為守護自然與文明的珍貴遺產指明方向。
2025年3月15日,《古樹名木保護條例》正式施行,這部我國首部針對古樹名木保護管理的行政法規,以法律的堅實臂膀,為“綠色國寶”筑起全方位守護屏障。每一棵古樹都是活著的歷史典籍,守護它們,就是守護文化根脈,延續文明薪火。
“前人栽樹,后人乘涼”的古訓,在鄭州這片熱土上化作跨越時空的生命交響。從阡陌交錯的農耕時代到鋼筋森林的現代都市,鄭州的古樹守護著一代又一代人,忠實地記錄著城市版圖的滄桑巨變。
中原網推出“古樹長歌·根脈中國——尋訪鄭州古樹”大型系列策劃報道。讓我們一起,去看看鄭州的古樹,就像去見一個久未謀面的老朋友,探尋它們所蘊含的歲月故事。
全城尋樹
您家巷口可有會講故事的百歲樹翁?
一棵古樹,一段往事,一腔鄉愁
如您有古樹線索可與我們聯系
我們一起守護城市年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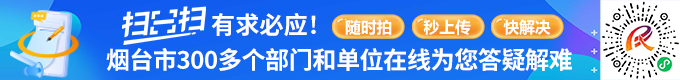


 2020年全國“放魚日”同步增殖放流活動在煙
2020年全國“放魚日”同步增殖放流活動在煙 山東滑雪高手匯聚“雪窩”煙臺 賽場飛馳比
山東滑雪高手匯聚“雪窩”煙臺 賽場飛馳比 2000余名民間藝人齊聚
2000余名民間藝人齊聚 以新姿態奔赴新征程
以新姿態奔赴新征程
